
【教育】美籍華人為何不太支持孩子學文科?
作為一名出生在矽谷的華人,我總感到自己似乎應該學習理科。畢竟我家位於蘋果和谷歌的大本營,我父母在九十年代為讀工程專業研究生而移民美國。
我從小在一個重視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被統稱為STEM)的環境中長大,因此一直著重學習數理科目。在初中時,我插進了一個數學快班。在高中開始前的那個夏天,我放棄了自己感興趣的本地藝術工作室開設的版畫課,提前自學了代數2和三角學。我周圍的許多華人同學希望像他們的父母一樣成為工程師。我也一直相信自己以後會在這個領域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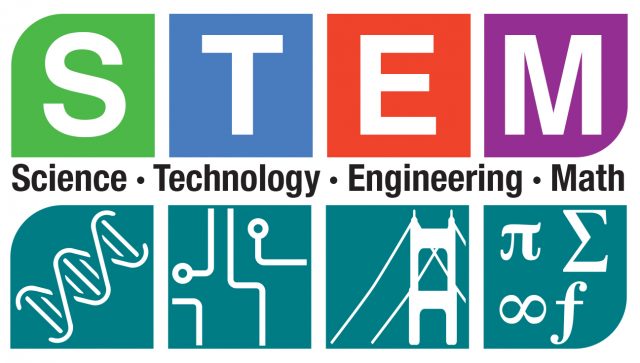
但在內心深處,我對數理化從沒有特殊感情。相比之下,人文和藝術才是我的摯愛。我從六歲起就在本地的藝術工作室上課;我發覺自己對創意性寫作抱有激情;我課餘的大部分時間都用來讀小說;除此以外我還在高中擔任了學校文學雜誌的編輯,暑假參加了寫作工坊。在伴隨我長大的理科環境和真正熱愛的科目之間,我搖擺不定。
進入少年時代後,我便一直經歷著這種掙扎。在身邊的華裔同齡人和親戚的口中,甚至有時在我的腦海中不停地重複著同一個看法:理解莎士比亞有那麼重要嗎?了解一個已經滅亡了的政黨有什麼用?在最近的一趟歷史課上,一位同學打斷老師:「如果我要當神經科醫生,為什麼要學習歷史?」類似這樣脫口而出的問題說明了一個疑惑:學習人文學科有什麼用?在我看來,這些問題聽上去有道理,實際上卻帶有些誤導。
這當然不是僅存在於美籍華人身上的問題。當今的美國學生和整個社會似乎越來越忽視人文學科的益處。美國文理科學院一個名為「人文指標」(Humanities Indicators)的項目報告顯示,2014年在本科修完核心人文專業的人數創1984年以來的新低。這個趨勢讓美國高等教育界在過去幾年憂心忡忡。
但想到我們的文明和歷史,這個問題就有點奇怪。眾所周知,中華文明一貫重視教育。傳統中國文化重視培養擅長琴棋書畫的人才,而當今的中國海外移民已經偏離了這種傳統。許多中國移民學習了數理化,於是他們也理所當然地鼓勵自己的孩子學習STEM科目。根據負責為美國大學招生設計考試的大學理事會(College Board)的調查,從1996年至2001年,有47%的亞太裔學生主修STEM科目,這個比例是白人、非洲裔和拉丁美裔學生的兩倍還高。一份2011年美國人口統計局的研究顯示,亞裔學生在與STEM相關的領域裡「比例極高」。
今年早些時候,我的英文課布置閱讀《哈潑斯雜誌》(Harper』s)上一篇由馬克·斯羅卡(Mark Slouka)撰寫的名為《去人性化》(Dehumanised)的文章。斯羅卡指出,美國「對藝術和人文扮演的重要公民職能地削弱……正將國民塑造成僱員,而非公民」。
這一切讓我不禁疑惑:華人既然如此重視教育在職場中的作用,為什麼有那麼多華裔父母會忽視歷史、藝術和文學的重要性?他們難道不懂得這些科目可以教給年輕人價值觀與道德準則,得以讓他們在社會中承擔責任,做出智慧的選擇,學會批判性思考,自由地表述自己的觀點嗎?我想起了歷史老師的一句話:「民主離滅亡總是只有一代人的距離。」在一個社會中,數百年歷史的民主理想,比如言論與出版自由,稍有不慎就能被鎮壓,乃至滅亡。
在舊金山灣區長大過程中,我發現華裔家長雖然常常鼓勵孩子把學習藝術當作愛好,但除非孩子真正在鋼琴或戲劇方面有所成就,許多人仍然認為人文學科沒有實際用途,找工作前景暗淡,工資微薄。我的一位華人同學就無法說服她的父母讓她參加藝術夏令營。他們希望她考慮理科項目,認為這樣更加實際。我還有一位華人朋友希望成為設計師。她在過去的一年中試圖說服父母讓她選擇和藝術相關的職業。在她最近的一件藝術作品中,她試圖表現華裔家長認為藝術行業徒勞無用、只能用來掙零花錢的偏見。她用硬紙板做了一個二胡的模型,並在上面貼滿了一元鈔票。

在課堂上,我注意到了中美文化的一些差異,比如大部分的中國學生都是恭敬地遵從老師的指導。
我的看法與上述偏見恰恰相反。我認為人文學科可以幫助培養批判性思維,而這種能力對於學習任何科目都至關重要。通過讓學生們學會獨立思考,人文學科教會他們如何面臨職場中的轉折。威斯利安大學校長邁克爾·羅斯(Michael Roth)將通識教育的這種功能解釋為對整個人的培養,而非僅僅教會一個人工作所需的技能。《高等教育紀事報》(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曾刊登羅斯在2009年一篇紀念威斯利安大學人文中心的演講。他在這篇名為《超越批判性思維》的演講中提到:「人文科目會給予你的內心和腦海必要的元素,讓你今後幾十年在完成創造性和集中性工作時都受益無窮。」創造性思維可以應用於包括STEM在內的任何領域,對人的一生都至關重要。Paypal的CEO彼得·泰爾(Peter Thiel)、時代華納的前CEO傑拉德·萊文(Gerald Levin)和Flickr的前創始人之一斯圖爾特·巴特菲爾德(Stewart Butterfield)的經歷都證明了這一點。《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雜誌在2014年的一篇文章將包括他們在內的一組人命名為「九位學哲學出身的著名總裁」。
我自身的成長和成熟也來自於文科的學習。我的文學老師曾說過,人們直到在家門口看到磨難才學會同情。作為生活在發達國家的學生,尤其身處於像矽谷這樣一個富裕的象牙塔環境中,我從未目睹過飢餓、戰亂以及內亂。因為我沒有經歷過這些人間苦難,我便將人文學科當作一扇窗戶,來透視我在現實中無法擁有也不想擁有的經歷。
比方說,在名著《紅字》(The Scarlett Letter)中,作者霍桑(Hawthorne)借他的主人公海斯特·白蘭(Hester Prynne)之口說出了一句肺腑真言:「她也擁有許多人一生的渴求,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經歷一場深刻的悲痛,以此來升華她的人性,讓她對他人的悲痛感同身受。」霍桑希望說明感情上的傷痛能夠升華一個孩子的天性,讓她體會他人的傷痛。讀者們也能通過這樣的情節感受培養自己與他人建立共鳴的能力。

於是我明白了文學在社會改變中固有的角色。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的《湯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在廢奴運動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的《另一半人怎樣生活》(How the Other Half Lives)為城市窮人帶來了社會變革;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奧秘》(The Feminine Mystique)啟發了現代女權運動。
近期,911恐怖襲擊後美國通過的《愛國者法案》(USA Patriot Act)加強了政府監控權,許多美國人感到這是對他們受憲法保護的隱私權和言論自由權的侵害。美國人意識到,如果沒有有教養的公民意識到自身自由受到的威脅,社會將會退化成喬治·奧維爾(George Orwell)在小說《1984》中所描述的反烏托邦國家。
高中二年級時,我為了自己的學術前途向一家大學諮詢公司的華裔顧問尋求意見,他居然告訴我:如果你的數理化不差,為什麼要學文科呢?
我是這樣認為的:
文科是培養有認知的公民必不可少的科目。它教會人們通過間接經歷學會體會他人的情感,它培養的批判性思維在所有行業中都可以應用。只有通過接受領會人文學科所提供的一切,社會和個人才能真正強大。











